
是父子,也是學長學弟
帶聽損孩子除了和一般孩子一樣得細心呵護之外,還有額外的療育課程要學習;我和小杰的媽媽都是聽損者,不但要克服自己的障礙,還要獨力教導小杰的聽與說。
我是彥華,二十四年前我三歲的時候,在位於台北市長沙街的惠幼托兒所聽障班(婦聯聽障文教基金會前身)接受聽語訓練。現在我兒鴻杰將近兩歲了,也在婦聯基金會接受早療,我與鴻杰都有先天性聽損,父子倆可以算是學長學弟。
小時候因為我對鞭炮聲沒反應,家人覺得疑惑才被診斷有先天性重度聽損,在爸爸、媽媽悉心教導以及許多貴人的幫助下,健康地長大成人,然後和許多人一樣步入人生下一階段—結婚生子。
當我與太太歡喜迎接新生命到來時,我兒小杰沒有通過新生兒聽力篩檢;當下心情雖然慌張,但還是強作鎮定安撫家人,「也許是羊水塞住耳道才會沒通過吧!」但隨著幾次聽力檢查結果都在55分貝左右,事實擺在我們眼前,我們接受了兒子也是聽損的事實;所幸小杰聽損程度比我輕得多。
我們開始思考要做些什麼來幫助他。先在網路找資料,查到嬰兒在六個月大之前開始做早期療育,效果是最好的,所以我們在小杰還沒六個月大時,就開始帶他到基金會做早療,持續到現在。
以前從不知道照顧孩子的辛苦,是從開始帶小杰做早療之後,才知道在我小時候,小杰的爺爺、奶奶帶杰爸我有多麼辛苦。帶聽損孩子除了和一般孩子一樣得細心呵護之外,還有額外的療育課程要學習;我和小杰的媽媽都是聽損者,不但要克服自己的障礙,還要獨力教導小杰的聽與說。每週到基金會上課時,要記住老師上課的內容,回家後還要利用時間持續地教導小杰。小杰年紀小,喜歡跑來跑去(爬來爬去?),手能碰得到的東西都會抓,還會扯下助聽器,我們得一直「盯」著他的一舉一動,長時間下來真的不輕鬆,這種情況跟杰爸我小時候接受語言訓練時還真是像極了。
經過兩次ISP會議,老師提醒我們,小杰進度有點落後,而且也變得不愛發出聲音,懷疑是孩子開始會害羞了,還是教導的方式需要調整。於是我們改變了帶小杰的方式,像是口手語並用跟他對話,或是遊戲時,爸爸用很誇張的表情、動作聲調引起小杰興趣。每天早上和下午分別撥出30分鐘左右做老師交代的功課,特別是詞彙的部份(因為爸爸媽媽常用手語,詞彙量可能沒有那麼豐富)。老師交代的功課會有好幾個詞彙,我們就每天隨機地講,讓小杰的詞彙量累積起來,也許就會說話了。另外,課輔老師建議可以托兒半天,中午回家;回家後在家上課或一起做家事、玩遊戲,聲音刺激多,進步就快,這是我們要努力的方向。
回想我小的時候,父母會教我跟生活相關的手語;吃完晚飯看電視新聞,我也會問爸爸、媽媽字幕在說些什麼,爸爸會看一句再比一段手語來讓我知道意思,所以還沒上小學之前,我已經可以知道字幕大概的意思,但還不會寫字。到了小學開始學寫字,也經由手語了解字的意思,因此在學習國字上沒有遇到障礙。
小學二、三年級早自習時,特教班老師每天早上都會給練習本,練習造句、填詞、辨錯別字等。剛開始時,我寫得慢、又錯得多,到後來越寫越快、也寫得越好,老師乾脆印厚厚一疊練習本給我練習,就這樣建立了基本語言能力,再加上我很喜歡看課外讀物,國小三年級還獲得借書王的獎項,閱讀對我的幫助很大。
我的聽力很重,雙耳聽損大約一百分貝,戴助聽器只能聽到中低頻率的聲音,高頻率的氣音都聽不到,所以小時候不知道空氣流動是有聲音的,我只會發有聲的聲音,老師怎麼教還是學不會。直到上大學接受語言訓練後,才知道氣音的概念,並試著在完全聽不到氣音的情況下,學習氣音以及各種注音符號正確唸法。二十歲時,我開刀植入人工電子耳後才開始聽到氣音,原來聽起來是細細的,之前完全沒聽過。雖然唸大學時一直有在進行語言訓練,但是出社會後忙於工作,訓練就變得斷斷續續。不過,雖然我的口齒清晰度不算好,只能勉強做簡單的口語溝通,但有了手語及筆談的輔助,也填補了外界訊息吸收不完全的缺口。
我兒小杰有聽損問題,要花很多時間及心力來教育小杰,可是實際做來,真的沒有那麼簡單,所以我跟杰媽有很大進步改善空間,需要耐心一步步地去做。身為父母當然會希望小孩可以健康地長大,我們也希望聽損對於小杰的影響能減到最小,期望小杰長大以後可以有更多空間可以揮灑。
這些是我的經歷,希望可以提供大家做參考,也希望能對大家有幫助。
在此要感謝婦聯過去三十年對聽損教育上努力及堅持,到了今天仍有很多人受惠,其中也包括杰爸跟鴻杰。還記得以前彥華在長沙街上課,是金老師跟田老師在帶我們這一班;彥華畢業後,金老師仍持續為聽損教育一直付出、貢獻到今天,彥華感到驚訝又佩服,實屬不容易,也謝謝她們!金明蘭老師更是從小看到我長大,一直都有在連繫,這很珍貴。
祁彥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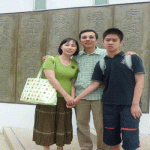 跨越鴻溝,心口相通—那些年,孩子教我的事
跨越鴻溝,心口相通—那些年,孩子教我的事  不幸中又非常幸運的奇蹟
不幸中又非常幸運的奇蹟